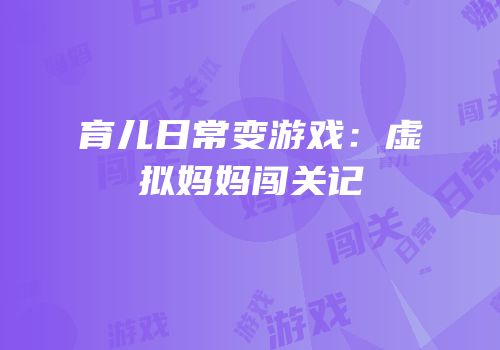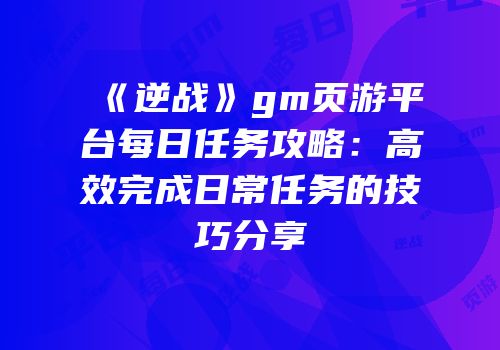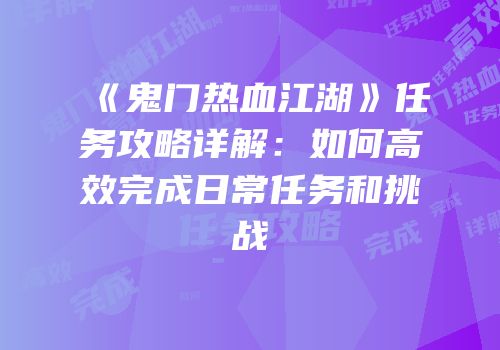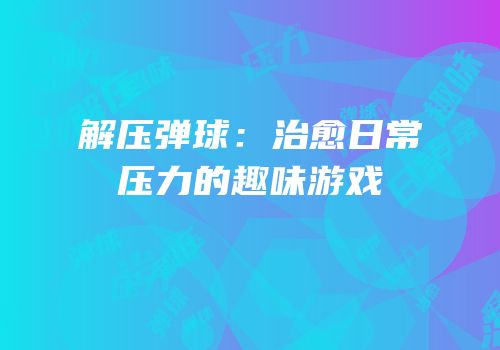拳头比脑子快的童年
我老家客厅墙上至今留着个拳头印。那是十五岁那年,我把同学鼻梁骨打断后,父亲抓着我的手往墙上砸出来的。石灰簌簌往下掉的时候,他喘着粗气说:“拳头硬不算本事,能把人按住了不揍才算能耐。”可惜当时的我,满脑子都是游戏厅里那个说我妈坏话的小子跪地求饶的样子。
在建筑队家属院长大的孩子,解决问题的方式就像工地上的钢筋——直来直去。记得有年冬天,邻居家的狗叼走了我准备送给班主任的腊肉。我抄起晾衣杆追着狗跑了三条巷子,最后被狗主人举着铁锹堵在死胡同里。要不是闻讯赶来的母亲赔出去两瓶香油,那年期末考试的考场大概要设在派出所。

- 1998年:小学五年级,第一次用板砖拍哭抢我弹珠的混混
- 2003年:初中部打架冠军,教导处常客
- 2007年:因为食堂插队把餐盘扣在同学脸上
那根白头发成了导火索
真正让我愣住的是大二寒假某个清晨。母亲在厨房熬腊八粥,我照例睡到日上三竿。被蒸汽熏花的眼镜片后,突然有根银丝在她鬓角闪了下。我鬼使神差地伸手去揪,她却猛地缩脖子:“别闹,正看着火呢!”
这个躲闪动作让我想起九岁那年——我把不及格的数学卷藏进米缸,她举着扫帚追出来时,我也是这样本能地缩脖子。原来在朝夕相处的人之间,伤害就像砂纸,经年累月地打磨着彼此的形状。
| 野蛮时期沟通方式 | 温柔时期沟通方式 |
| 摔门而出 | 主动说“我需要冷静十分钟” |
| 吼叫式反驳 | 先重复对方观点确认理解 |
| 冷战三天起步 | 两小时内发起对话 |
改变比挨打还疼
报名参加社区调解员培训那天,培训老师让我们玩了个“说反话”游戏。当同桌的大妈故意说:“你们年轻人就是没责任心”时,我攥紧的拳头在裤兜里直发抖。但按照规则,必须回答:“您说得对,能具体说说哪件事让您这么想吗?”
这种别扭的对话方式,就像给野马套笼头。有次在超市,撞见插队的大哥理直气壮地说“急什么急”。我深呼吸三次才压住火气,结果人家看我脸色不对,反而主动让出了位置。
- 随身携带薄荷糖压制怒火
- 手机壁纸设成“话到嘴边拐个弯”
- 每周给父母发三条关心短信
现在的日常
上周同事老张误删了我做的报表。要是搁以前,我早拍着桌子问他是不是存心找茬。但现在会先泡两杯茶,等茶叶舒展开再开口:“张哥,咱俩对对工作流程,看哪个环节能加个保险栓?”
昨天路过游戏厅,听见几个半大孩子嚷嚷着要找人算账。我多管闲事地买了串烤肠凑过去:“哥几个知道吗?派出所新装了人脸识别摄像头,拍苍蝇都能看清公母。”看着他们讪讪离开的背影,突然想起父亲当年砸在墙上的那个拳头印。
窗台上的绿萝又抽新芽了,母亲在电话里念叨着要给我寄新腌的雪里蕻。春风裹着楼下小贩“磨剪子嘞”的吆喝钻进来,混着厨房飘出的土豆烧肉香气——此刻的温柔,比年少时任何一场“胜利”都来得踏实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