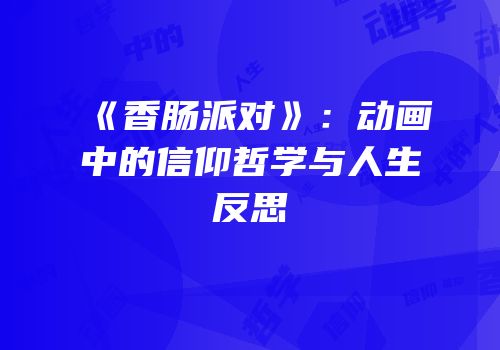卯时三刻,李顺佝着腰穿过永巷,青砖上浮着一层薄冰。他数着步数停在第七块裂砖前,袖中油纸包着的药渣恰好落进缝隙——这是今日第三次替贵妃清理痕迹。
顺公公,翊坤宫的墨锭该换了。"小宫女捧着漆盘发抖,盘底压着张洒金笺。李顺眼皮都没抬,右手接过漆盘的瞬间,左手食指在笺角轻轻一折,暗纹牡丹缺了片花瓣。这是淑妃要买通御药房的暗号,他得赶在申时前把消息透给皇后身边的画眉姑姑。
三更梆子响过,李顺对着铜盆净手。胰子搓到第三遍时,窗外传来布谷鸟叫。他推开西偏殿的暗门,十二盏连枝灯照亮满墙密格:左边第三列第二格收着各宫主子的月信簿,右边第五格码着三年间的冰敬炭敬单,最底层的铁匣锁着东厂密报——那里面有两广总督与宁王世子换过庚帖的记录。
腊月初八,李顺升任司礼监随堂太监。接印那日,他在袍服里多穿件细葛短衫。当掌印太监王瑾拍着他肩膀说"年轻人该多历练"时,他后背瞬间沁出的冷汗全被葛布吸走了。毕竟十年前净身房那个雪夜,王瑾往他伤口撒的可不是止血的白药粉。
宫灯将李顺的影子拉得老长,像条蜕了皮的蛇蜿蜒在朱墙上。他数着新得的东珠,突然想起入宫时老太监教的规矩:在紫禁城,活人得比死人安静,聪明人要装得比傻子愚钝。瓷枕下的《春秋》翻开到僖公二十八年,书页间夹着张当票——城南当铺丙字柜,存着他二十年前的名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