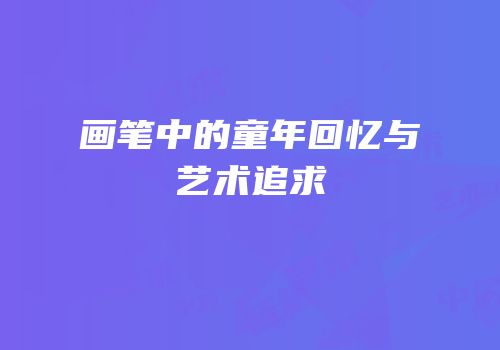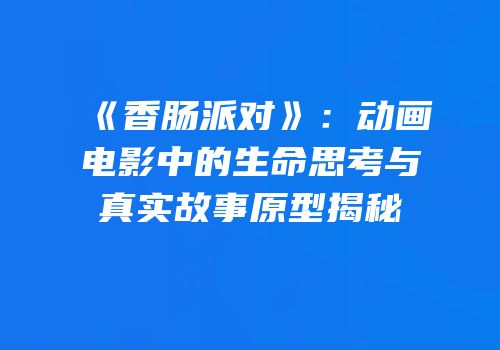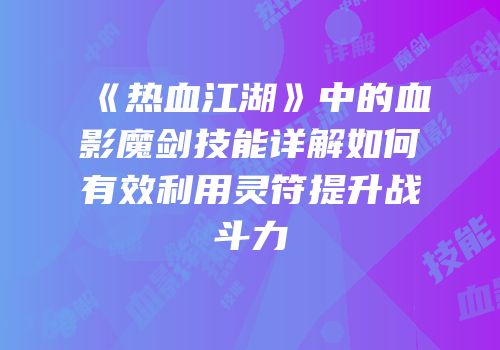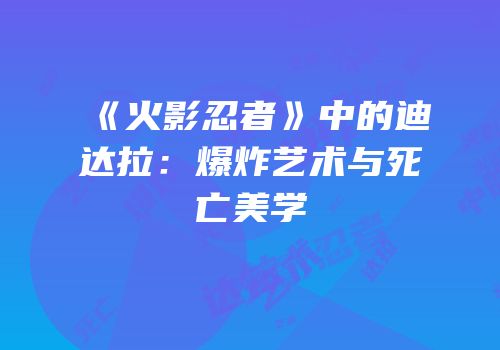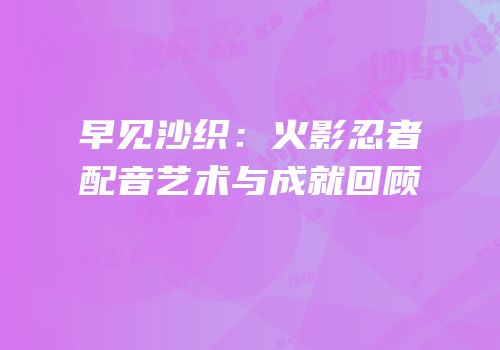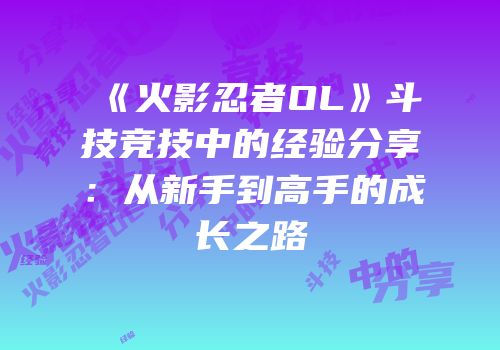窗台上那支掉漆的木质画笔,总让我想起十二岁那年的暴雨天。当时蹲在少年宫画室的走廊,透过门缝偷看艺考生们挥动画笔的模样,潮湿的霉味混着松节油的气息,像颗子弹击中了我的心脏。
被封印的童年天赋
记得小学三年级的美术课上,我用彩色铅笔画了幅《蚂蚁搬家》。教导主任举着那张皱巴巴的画纸,在走廊里来回走了三趟,最后蹲下来问我:「你爸是美术老师?」其实我家三代都是卖早点的,蒸笼里的白雾比颜料更熟悉。
- 2004年:用酱油在厨房瓷砖上画了第一幅「壁画」
- 2006年:班主任没收了32本涂鸦作业本
- 2008年:用粉笔在巷子口画了条3米长的「巨龙」
那些年被毁掉的创作
| 作案工具 | 创作场地 | 存活时间 |
| 圆珠笔芯 | 数学课本插图 | 3小时(被数学老师发现) |
| 烧火炭 | 老宅白墙 | 2天(春节前被重新粉刷) |
| 指甲油 | 卧室木地板 | 17小时(母亲拖地时溶解) |
青春期颜料暴动
初二那年用压岁钱买了套盗版水彩,躲在储物间调色时被父亲撞见。他拎着沾满面粉的擀面杖站在门口,影子被夕阳拉得老长:「画这些能考上重点高中?」那天夜里,24色颜料从二楼窗户飞出去,在水泥地上炸成一片星空。
绘画工具进化史
- 铅笔时代:0.5元一支的中华牌,笔杆缠满胶布
- 炭笔时期:总把校服口袋染得漆黑
- 水彩阶段:调色盘结的垢比颜料本身还厚
成年后的疯狂实验
工作第三年租了个地下室当画室,有次用丙烯画海浪,从周五晚上画到周日清晨。房东来收水电费时,发现我正对着干涸的调色板啃生胡萝卜——那幅画的蓝色深深浅浅铺满整面墙,像要把人吸进海底。
| 创作状态对比 | 学生时代 | 成年时期 |
| 作画时间 | 课间10分钟 | 连续38小时 |
| 颜料消耗 | 每月1管白颜料 | 每周3支钛青蓝 |
| 后遗症 | 右手小指侧边墨渍 | 肩周炎+色觉敏感 |
那些停不下来的瞬间
去年用油画棒临摹《星月夜》,画到东方发白才发现手指磨出血。颜料嵌在指纹里的灼热感,竟比完成作品更让我着迷。参考鲁道夫·阿恩海姆在《艺术与视觉感知》里说的,这大概就是「视觉张力引发的生理性震颤」。
画笔构建的平行宇宙
现在我的衣柜里挂着五件沾满颜料的围裙,从樱花粉到象牙黑层层叠叠。每当站在画布前调色,耳边就会响起十二岁那天的雨声,潮湿的水汽裹着松节油的味道,在鼻腔里酿成陈年的酒。
阳台上的薄荷草又枯死一盆,但调色盘里新调的翡翠绿正在发光。楼下的早餐铺飘来芝麻香气,我握着画笔的手悬在半空,突然想起今天还没吃过早饭——不过没关系,画布右上角那抹橙黄,看起来和刚出锅的煎包一样美味。